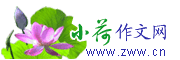学习时,时光总是流逝的飞快,“叮铃铃”的下课铃不懂事地乱叫着,硬拉着将我从知识的海洋中拽了出来,而我也不得不向亲切而可爱的书本们暂时道一声别了——已经是下午的放学时间了。
周围的同学们如百米赛跑时听到了号令声的运动员一般飞似的跑了出去,我却不慌不忙地整理好杂物,这才缓缓起身,因为我知道:跑得快不一定赢,不跌跟头才是成功。这样想着,我来到了走廊,望着空无一人的过道,我不禁思考起人生之意义等一些哲理问题。正当我想得起劲,”哐当“一声,由一班传来的噪音将我拉回了现实,我疑心有猫猫狗狗之类的小动物窜进了一班,乐于助人的我第一时间冲到了一班门口,准备将罪魁祸首捉拿归案。可是,呈现在我面前的依然只是一间平淡无奇的教室。这时,夕阳的余晖晃了晃我的眼睛,我这才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了,是时候去吃晚饭了。
我转过身来,却迎面刮来一阵阴风,沿着走廊,将各个教室的窗帘都从窗户里面吹出来了。隐约之中,我仿佛看到一个人影闪过。来不及细想,我从一班门口向楼道大厅的楼梯口径直走去。正当我要走过二班后门的时候,一只粗壮、黝黑而有力的大手从门中伸出,拦住了我的去路。我正感困惑,准备进门一探究竟之时,那人竟自己走了出来。
当我看到他的真容后,即使是一贯冷静而理智的我也不禁为之一震——他便是高二一班有名的张梓焯!自封雅号“野猪”,生性残暴,在二中,不管你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的,见了他,都必须喊一声“猪哥”,不然的话,一班那个拄着拐杖的,还有二班那位胳膊上缠着绷带的,便是再好不过的、血淋淋的例子。
猪哥的左手拿了一份一笔未动的英语报纸,他用那肥大的右手指了指手中的报纸,又指了指我,随即便摊开了手掌。我大概看出来他是在向我索要英语报纸来供他抄作业,然而我绝非那种会向强权低头的人。我冲他摇了摇头,走过去将他顺手推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刚走出没几步,我便感到周围的空气似乎寒冷得有些诡异。我猛然回头,只见一块板凳直直地朝我面部飞来,我连忙伸手接住。“哼!”猪哥懊悔地跺着脚,整栋教学楼都为之颤抖。猪哥这套背后偷袭的小动作着实激怒了我,我顺手抄起三班门前的一张桌子,尽全力对着猪哥照面砸去,谁知猪哥虽然体型庞大,其灵活性却丝毫不下于我。只见他身体后倾,紧接着便是一个下腰。我尽全力甩去的那张桌子竟贴着他的肚皮滑了过去,砸到了二中旁边一家出租屋的房顶。猪哥站起身来,看到了我的“杰作”,得意地笑着。笑着笑着,他却一个箭步冲到我的面前,举起拳头,劈面朝我死命打来。我哪里料到野猪还有这一着?情急之下,我只好用出那招:低下身子,一把抱住猪哥腰间,随之往后一仰,给猪哥来了一套“German Suplex(德式拱桥摔)”,这一摔放平常人来说倒也还好,可放在猪哥那重达两百斤的身躯上,落地时接近10个g的加速度,着实让猪哥吃了回苦头。
猪哥挨了我这一下,痛不欲生地躺在地上,眼中充满了不甘的泪水,嘴里却还不住地求着饶,我走上前,没有一味地斥责他的过错,反而帮他擦干了眼泪,悉心教导起来。临走前,我注意到,猪哥的眼角,似乎再次湿润了。
此后,从前那个为非作歹、肆意妄为的猪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位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的三好少年。与此同时,种种传说也开始流传开来:有人说猪哥原本就是个好学生,只是不幸被猪魔上了身,那日下午学校来了个杀猪匠,给那猪魔吓得从此不再敢出现了……只有我知道,真正改变的猪哥不是我,也更不是什么杀猪匠,而是张梓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