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指数 <音乐与文学>有一种当初写《人生若只如初见》时的那种感慨,同样是与一个人的一种告别。真实故事。 | ||
 几个月前,我发了一条说说,让别人帮我翻译一首英文歌的名字。 那首歌叫做《Someboby That I Used To Know》。 我把这首歌介绍给她时,是高一结束时的那个暑假。因为一个诺言,如果我那次暑假前的期末考试化学能考上80分,那我就请她吃一顿。 最终我也因为实现了目标而履行了诺言,也正是那次聚会,我告诉了她这首歌。 只是当时,我们已经认识了四年。 我与她是三年初中同班同学,高一的时候我们隔壁班。 记得刚上初一的时候,老师问班上有谁练过书法,我举了手。结果,老师让我把一些同学的名字写在他们的校徽上。后来,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会记得当初有一个人把她校徽上的名字写那么丑。我也只能无奈地笑笑,这种记忆倒也真的足够难忘。 有一次,我和她被老师安排搭档去参加县里的演讲比赛。我很意外,也很紧张,于是到了周末,我们两个人就到学校的生物园里练习,或许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她有了几份默契。 然而,当我们终于将演讲稿练习得能够上台表演时,却被告知演讲比赛取消了。 我们百感交集,庆幸也又遗憾,少了一次出丑的机会。 记不起是初二还是初三,我们慢慢熟络,她是语文科代表,于是常常去办公室的时候顺手帮我交迟做完的作业本,放学的时候,她总会等我,然后我们顺道一起走,我和她无话不谈,我把她当成了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那时,我并没有想过是否有一天我们会决裂。 初三的时候写同学录,她是第一个在我那本同学录上留言的人,写了三页,她说会一直记得我的零食,希望高中还会是朋友。 然而那些小小的憧憬,终究在两年多以后,我翻起那本同学录时才发觉,原来有些以为理所当然的愿望,还是会灰飞烟灭。桐华说:“想得到的都拥有,得不到的都释怀。” 高一那次暑假,我和她听着那首歌时,都不知道那首歌的含义。甚至过了好久,我才理解了那首歌的名字。 有人翻译成故人。 You didn't have to stoop so low 你不必如此屈从隐忍 Have your friends collect your records 让朋友来帮你打包行李 And then change your number 然后更换了电话号码 I guess that I don't need that though 我想我也不需要知道它们了 Now you're just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现在的你只是我生命中曾经熟悉的一个过客而已 我才明白,原来很多故事,早有前兆。世界上的每种巧合,其实都是必然。我们都知道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种种坎坷,可是还是有那么一刹那,我侥幸地希望,我和她可以不要有那些羁绊,至少我们可以一起走到高三,即使分道扬镳,也就不会有遗憾了。可是我知道不会有那种假设,更何况这份告别,是我自己做的选择。 我想,我会一直记住,在我们走过的漫长岁月里,最终因为我的偏执,她的善良被利用,让我们失去对彼此的信任。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格格不入,连见面的寒嘘都刻意恭维。因为某人的缘故,我和她,变成了有隔阂的陌生人。原本只是我跟别人的矛盾,她却选择了相信别人。当我把话说清楚时,她大声地说,别人做错理所应当,毕竟我当初也是那副嘴脸。 我终于明白,原来,时过境迁,有些物是人非,已经是定局。我也知道已经不用再费口舌。我只在乎结局,从不在乎过程。 许多往日里的嘘寒问暖,终究成了擦肩而过时的目光闪躲。提及她时,只是一个寻常的某某。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都猜不到结局。 《你好,旧时光》里有一句话:“同伴,不一定非要走到最后,某一段路上,对方给自己带来的朗朗笑声,那就已经足够。” 生命中那么多过往,来来去去,没有谁长久地互相陪伴,无非只是某些岁月里,一个一起走过某些路途的某人罢了。而往后的时光里,那些某某,还会很多。 高二下学期的时候,班里举行了一次班会活动。她是主持人,念完台词,她就走到了教室门边。 最后是击鼓传花游戏,拿到花的要到讲台上唱歌。 几个同学轮番上去唱了歌,直到最后一个女生站到讲台上。 那个女生选了陈奕迅的《十年》。起初女生唱得有点跑调,但是大家却很安静,渐渐地,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唱起这首歌。 我不经意间看了她一眼,发现她似乎也恰好在看我,我迅速转移了目光。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下课铃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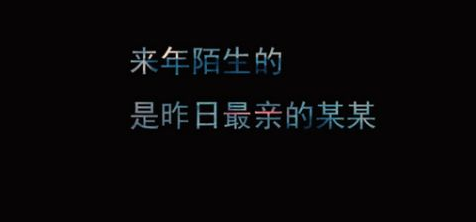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