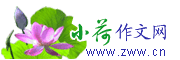你有没有爱过这样的一个人。他属于你最纯粹的感情信仰,他占据你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他有你着迷眷恋的干净容颜,他是刻在心口上的淋漓疤痕,你爱他,像是行走于一条光雾隐迹的茫途,不现前路,不见归途,除了举步维艰地前行,再无出路。
_
梦是灰色的。反复张开的口始终发不出任何声响,她赤着足站在滚烫烙肌的石块上绝望地看着视野里唯一一抹亮色走远,依旧是那样坚忍的背影,一步步地,像是在走出她的生命。耳边有不断像是水滴掉落石板的声响,滴答滴答,一声声砸落进心底。
南音躺在床上出神地看着窗外,有细碎的凉风掺着细雨越过窗隙发出轻响,她安静地睁着眼,侧身面向窗口的脖子仰成了僵硬的线条,眼角处隐隐约约闪现着水光。那些一直被刻意屏蔽的记忆猛然间像一张张幻灯片,走马流花般地缓慢播送着,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一帧帧图像滑过去。
_
南音首次见到徐洺生的那天,夙安镇正值黄昏时刻的雨后放晴,那时她正百无聊赖地蹲在大宅子的房檐下看镀了层金红色的天空,身后隐约传到母亲的叫唤声,她下意识地回头,正好看到夕阳照出的微弱光圈攀过树枝铺在母亲身边少年的肩膀上,连着他的米色衬衫也染上了层光圈,柔和地不可思议。恍惚间南音以为看到了挚爱的老旧画片里撑伞的那个男子。像蒙蒙细雨里淡淡的茶香,温馨而不浓郁,芬芳而无热烈。
那时她不过十五年岁。
_
徐洺生变成了南音的哥哥。在初次见面之后。当时的年代依旧无可避免地束缚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上,而单单只有南音一个子嗣。可是经济富裕的顾家毕竟需要一个男丁来充场面,于是徐洺生,或者该说是顾洺生便是这样一个起装饰作用的存在。生活真像是在时刻不停地往未知的歧路上行进,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对你来说算惊还是喜。如此突兀地出现一个人又突兀地闯入南音的生命,当时不能说是不排斥,哪怕徐洺生是南音初次见面便分外有好感的异性。
顾家大宅的面积实际上并不小,除却每日进食时刻的无可避免的碰面他们很少会有实际上的交集,那时的南音除了礼貌的叫声“哥”之外再不会有过多言语,听来亲近的称谓骨子里却礼貌到冷漠。怪异且疏远的模式却令他们相安无事地过了一年。
分明都是循规蹈矩地进行,是从什么时候感情开始变质。南音想。大概是那个时候了。定是那个时候。十七岁生辰时正巧是顾家姥爷大寿,那晚顾家宅子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前来祝寿的人,喜好清净的南音躲到大宅最偏僻安静的池塘透气,那晚的月色清亮是她最喜欢的摸样,南音独自一人在池塘边的假山上坐了很久,却没想到离开时由于坐的太久起身过猛泛晕着掉进了池塘里,碧深深的池水漫过头际时南音甚至连惶恐都还未来得及,手指紧抓成拳以为要死去时去却听到重物落水声,然后朦胧间有只手伸到了她身前,那只手仿佛带着光芒,点亮在了南音十多年的生命里,独一无二。
那是徐洺生的手。
_
醒来时窗边围了大群亲人,南音看到徐洺生就安静地站在人群最外沿,神情平静无波,宛若古井。耳边充斥着亲人的责骂,心底却有丝道不明的喜悦渐次渐烈地晕染开来,占据了全部感知。然后一切不言而喻,南音时常会去找徐洺生说话,说她的喜好说她的心情说她每日的点滴,很多言语好像也并不是非得说给一个人听,反倒像是她一个人的自语。
“宅外的梨花全开了,我很喜欢。”
“我在父亲那里搬了很多旧书过来,不知道其中会不会有你喜欢。”
…………
她细细地说其实并不在意徐洺生会不会有回应,却没想很偶尔抬头时会看到徐洺生倚在窗边极其认真的聆听摸样。也是从那时开始,南音不再称呼徐洺生哥,也不唤他洺生,只是会很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叫他的名字,“徐-洺-生”。
_
徐洺生。不是顾洺生。就像是潜意识地去执拗排斥承认些东西。那时她还是明媚少女,尚有勇气奋不顾身。
南音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在外人面前爆发了十几年来最强烈的情绪。顾家人看着平日里安静内敛的南音双眼通红一眨不眨地看着徐洺生,像是只被激怒的兽无法收敛起浑身的尖刺,而徐洺生只是沉默地低着头,延边低垂的发丝遮掩了全部情绪。
那年大学毕业的徐洺生未知会顾家便向学校申请去当时极其落后的西北支教,申请批准下来了,他消无声息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与南音渐行渐远的未来。
一切抗拒叫喧抵制最终没有改变徐洺生的决定。他不能带她走,也没有给她任何承诺。南音想,他的世界里,自己慢慢沦为了一颗挡路的石头,终究还是会被磨成一块圆圆的鹅卵石,再没有尖锐的刺,只能平稳地躺在他的过去和记忆中。
这是他的选择,是他对他们越见厚重感情的回答。
那也是南音最后一次见到他。
_
黑暗中南音大口大口地喘息,回忆就像刀子剜进心口狠狠转了一圈,疼痛终于失去了原本的刺骨,反而变得麻木起来,连什么时候抽走都不知道,却还是能够看到胸口的血肉模糊。时间隔的久了,那疼也逐渐淡了,可那样的感觉还在,形成的条件反射还在。她痛恨这样难以抑制的回忆,却找不到出口,整个人如同一条蛰伏在深海的鱼,漫无目的地航行前进,只为寻觅暗夜中的光芒,只为找到一股挣脱枷锁的力量。回想越多就越残忍,一次次的伤口裂缝。
徐洺生死了。死在了一片遥远的贫瘠之地上。死讯是在一年之后才传来,那年徐洺生任教的地域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死伤无数,当灾后死亡人数全部认定时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尸身无处寻迹,埋的都是些旧衣服。
时间好像是在那个时候瞬间停滞。南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三天,那些感情那些记忆那些与他有关的喜怒哀乐反反复复不停倒带,好像再不抓住些什么有个珍之又重的人便再也无迹可寻。三日后奄奄一息的她开了门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去看他。
我要去看他。
_
坐了很久的火车转了很多次大巴最后她是步行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了徐洺生的墓。那时已经是日落时刻,漫山高立的杂草,草隙间有不知名的小黄花娇弱地在闷滞的热风里摇摇欲坠。墓碑上没有照片,只写了他的名字。她一点点婆娑过去,跪在墓碑前手指顺着墓上的字迹描摹,一横,一撇,一捺…她写的异常缓慢,像是恨不得要让所有的时间都停滞在这一刻。
南音写着写着眼泪终是止不住簌簌地落下来,一滴滴泛着剔透的光。她把头伏在冰凉的墓碑上,一动不动地坐在墓前,直到朝露逐渐消散,直到曦光开始破晓,然后终于明白那个记忆里的安静少年,那个她珍之又重的少年,那个教会她爱的少年,终于不见。
回忆至此戛然而止。南音极缓慢地站起了身。她走到窗边,把掩着的窗帘掀开一角,窗外银晖的月光泻了一片,随着她渐渐把纱帘挑起,那光辉越演越烈,在窗前的书桌上渲染了一片银熠。
A Reason,Season,or lifetime。我才明白你的生命里总会遇见这样一个人。他无法陪你一生一世,他甚至不能陪你走过很多季节,他会在你生命最黯淡最孤独的时候唐突地闯进你的世界,陪你在梦境的荒野里逃亡,陪你在无星的暗夜里守着烛光,等你终于懂得爱懂得成长懂得珍惜后,他便会悄悄淡出,除了一地狼藉的回忆,什么都不曾留给你。
于是我只能蹲在地上,拾辍一地狼藉的回忆,努力把那些残破的流年拼接在一起。泛黄的纸,早已失却悲伤的质地。依稀的笑靥,依稀的温情。时间哗地过去,把一切凹陷凸起,统统碾平。